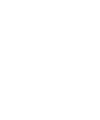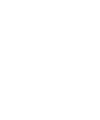殿下他病骨藏锋 - 第48章
厉锋沉默地掏出一块银子,扣在摊上。
商贩拿了银子,咽了口唾沫:“一人最多买十份。”
厉锋道:“那就十份,不用找了。”
“好嘞!”商贩利落地包好十盏素白的长明灯和笔墨,指了指旁边立着的小木牌:“为家人爱人祈愿,写下姓名和祝福语即可,心诚则灵。”
厉锋接过,指尖不经意擦过纸面,像怕惊了什么,力道放得很轻。
僻静巷口,一盏孤灯吊在檐角,烛火被夜风吹得摇摇欲坠,厉锋背对人群,解开纸扣,素白灯纸薄得几乎透明,能映出他指骨的轮廓。
“主子赎罪……不写名字,恐怕不灵验。”他在心里低念,声音压得极细,仿佛隔着胸腔与血脉,连自己都听不真切。笔尖蘸墨,腕子悬了片刻,才落下两字。
允明。
谢姓恐惹是生非,便只有名,这样反倒像偷来的私印,悄悄烙上灯皮。
墨痕未干,他先吹了吹,怕旁的灰屑溅上去,冲淡了那一点隐秘的亲昵。
可惜他不懂词,第一盏,他就写心想事成。
第二盏起,他连写八盏,字字工整,笔锋却一次比一次重,只有四个字——长命百岁。
墨香混着雨腥,在窄巷里悄悄发酵。
他写得专注,眉心微蹙,像在给某道密令加封,每写完一盏,便用手背轻轻压平纸角。
商贩终究没忍住,探头过来,笑得有些揶揄:“爷是给心上人求的?”
厉锋头也不抬:“不是。”
商贩心里直犯嘀咕,那灯纸上反反复复好像都是一个人的名字,一笔一划写得比佛经还虔诚,一个冷面煞星似的汉子,替同一个人祈福,若非心上人,还能是谁?
他偷眼再瞧,想看看是不是哪家贵女,却被厉锋察觉,凶狠地瞪了回去。
商贩也怕惹是生非,立即走人。
“等等!”可厉锋却扭头将他叫住。
“爷,您还有什么事?”商贩问。
厉锋提腕顿住。
墨尖悬在纸上,颤也不颤,这第十盏空着,空得他心口发闷。
“如果是求姻缘的话……写什么话最灵验?”
他问。
商贩陪笑,立即取了块写着字的牌子来:“自然是良缘由夙缔,佳偶自天成啊!这个最灵!”
厉锋嗯了一声:“好,多谢。”
当即又给了商贩一块银子。
他俯身,最后一次写下允明二字,笔势却比先前都缓。
——良缘由夙缔,佳偶自天成。
墨字并排,像并肩而立的两个人。
写完,他耳根已悄然泛红,却被夜色掩得严实,他盯着那行小字,眼底浮起一点极暗的火光,万一……那佳偶二字,能落在他自己身上呢?
火折子嚓地划亮,他先用手掌拢住风,再俯身点灯,火舌舔上纸缘,微微颤动十盏灯,一盏接一盏燃起,他双手托起,灯纸被热气鼓得饱满,轻轻碰撞他指尖,像欲言又止。
眼见得长明灯都变成遥远天际模糊的光点,再也看不见,他才轻轻舒了一口气,转身快步离去。
他想能快些见到谢允明。
第36章 采男人的周大盗
紫宸殿内,烛火摇曳,将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皇帝负手立于窗前,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,声音低沉而慎重:“南下之事,不宜声张。朕只召你二人前来,便是要秘密行事。”
微服私访也是个表现的机会,三皇子心底是高兴的:“儿臣明白,定当谨慎行事,为父皇分忧。”
谢允明微微颔首:“儿臣接旨。”
因着秦烈近日护卫宫禁颇为得力,加之皇帝将谢允明也带在身边,总觉得几个大内高手在侧仍不放心,便特命秦烈一同随行护驾。
同时,一道密旨已发往林品一处,擢升他为巡按御史,命他携官印一同随行。到时候由他与地方州县接洽,督察治水事宜,更为便利。
启程之日,天尚未透青。
秦烈作为此行领队,是唯一知晓最终目的地的人,一行人早已换下宫装,扮作南下的商户。
皇帝蓄了短须,自称老爷,谢允明是大少爷,三皇子改口三少爷,霍公公弯腰成了老仆,张院首戴起圆镜,扮作账房,秦烈玄衣束带,做了管家。
皇帝环顾众人,新奇地挑眉:“朕——啊不,我听着明大少爷倒是顺口,此行便姓明了。”
谢允明含笑道:“明老爷听着也很气派啊。”
皇帝却板起脸:“错,你怎么能叫我老爷?”他指了指自己,“你该叫我什么?”
谢允明垂目,轻轻唤:“爹。”
皇帝朗笑,一掌轻轻拍在他肩上:“这才像话!出了门,就得有个家的模样,可不要说漏嘴了,不然可要受罚。”
众人应是。
秦烈见时辰已到,上前一步:“老爷,大少爷,三少爷,车马已备妥,可以出发了。”
众人上了各自的马车。
谢允明特意请了旨意,带上厉锋,他与厉锋,以及奉命同行的新任巡按御史林品一,共乘一辆马车。
马车辘辘前行,驶出了巍峨的皇城,将京城的喧嚣与权谋暂时抛在身后。
车厢内,因脱离了皇宫那无形的枷锁,气氛比往日松快了些许。
林品一在谢允明面前,早已不复最初的拘谨怯懦。
或许是在御前历练久了,那双原本带着纯粹书生气的眼睛,也沉淀出几分精明与沉稳。
而他看向谢允明的目光里,偶尔会闪过一丝不易捕捉的探究。
他改换了称呼:“大少爷。”
“听闻您前些日子似乎又欠安,下官心中挂念,却未得机会探望,心中实在歉疚。”
“也不知……先生如今贵体可康健了?”
“你到底是关心我呢,还是关心你先生?”谢允明正倚着软垫,闻言,问道:“怎么,我竟不知,国师身体也抱恙了?”
林品一眉头微蹙:“其实,下官也不敢断言,只是前次收到先生回信,那笔走龙蛇的字迹,似乎不如往日那般沉稳有力,笔锋偶见虚浮……下官揣测,落笔之时,先生或有些许不适。”
谢允明闻言,只是极轻地叹了口气:“国师心系黎民,为国操劳,夙夜在公,却从不言自身辛劳,实乃我等楷模,令人感佩。”
林品一语气诚恳:“先生若有恙,我却不能侍奉左右,分担万一,实在羞愧难当啊。”
谢允明宽和地笑了笑:“林大人不必过于挂怀,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,好与不好,终究依赖自身元气与药石之功,旁人再是心急,亦是无法。”
林品一看着他这般无懈可击的模样,心中的那点怀疑如同细针投入深井,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激起,只得顺势笑道:“大少爷说得是,是下官心急了。”
“先生昔日也曾教诲下官一言,身处迷局,心若明镜,方可不染尘埃。”
谢允明点头:“说得好。”
林品一心中暗叹,继续道:“说来也怪,先生平日里待人,无论是对下官,还是对其他同僚,言辞往往一针见血,犀利透彻。可在那信笺之上,却总是循循善诱,耐心细致,简直,判若两人。”
厉锋截了话头:“那岂不是要恭喜林大人,得以窥见国师不为人知的温和一面。”
“这是好事,林大人何必纠结呢?”谢允明唇角微弯,弧度极淡,却像雪里一轮月色,映得人心口发凉。
他不再接话,侧首望向窗外,夏野后退,绿浪翻涌,风从帘隙钻入,吹得他眸色深浅不定。
林品一见状,深知再问下去也是徒劳,谢允明气度之从容,远非他所能轻易窥探,可心底那粒怀疑的种子却生根刺骨,朝会他与国师日日相见,国师步履稳健,声音清朗,何曾有一日病容?
真正病过的,从头到尾,只有眼前这位笑意温润的大少爷了。
皇帝一行,车马劳顿,在官道与崎岖小径间辗转了近一月光阴,抵达了江宁府一带。
沿途所见,触目惊心。
衣衫褴褛的流民拖家带口,面有菜色,询问之下,多言是从江宁周边城镇逃难而出。
问及缘由,却不是受水患所扰,说是人祸,没有田种不了地,没粮食就得逃命。
皇帝见一路颠簸,风尘仆仆,又担心谢允明身体吃不消,此地流民来源集中,问题显然根植于此,便决定停留此地,为巡查重点。
一行人入了江宁城,霍公公立刻寻了当地牙行,花费不少银两,租下了一处据说是前朝某位致仕官员修建的园林。
那园子位置尚可,看似清幽,但岁月侵蚀的痕迹明显,朱漆剥落,廊柱泛黑。
此地细雨如烟,绵绵不绝,不像北方的雨那般爽利。反而像是极细的牛毛,空气里弥漫着一种粘稠的湿热感。
皇帝在园中缓缓踱步,霍公公举着油纸伞亦步亦趋。
皇帝看着廊檐下结着的蛛网,和庭院石缝中倔强探头的青草,不由失笑,指着霍公公开玩笑:“你这老货,银子怕是扔进水里了,瞧着倒像是请咱们来给这园主当免费的花匠杂役了。”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