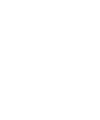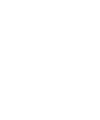三十是孩子,五十岁复婚也正好 - 第24章
后来,她只是蹲在花坛边上哭了起来。她怕看见林志风失望的眼神,更怕史秀珍的责备。
当天晚上,郑美玲翻出雪球用旧的新华字典。她的手指在纸页间轻轻摩挲,最后停在了“晨”字那一页。
“晨光”——清晨的第一缕阳光,多么温暖的名字。就像邻居们常说的,给流浪猫狗起了名字就再也舍不得丢弃。
她暗自下定决心:既然给孩子取了名字,就一定要把他平平安安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来。
偷煤的前一天夜里,林志风把攒下的两千块钱都还给了乡下老舅。郑美玲望着空荡荡的煤棚,又看了看雪球冻得通红的小脸上挂着鼻涕,心里空,也疼。
从火车皮下来的那晚,她做了奇怪的梦:铁轨旁站着一个穿棉袄的小男孩,背影和雪球小时候一模一样。她拼命想追上去看个清楚,双腿却像灌了铅似的动弹不得。
外面警笛声此起彼伏那晚,郑美玲慌忙间把那袋煤塞进了酸菜缸。她缩在炕角,直到外面没了动静才昏沉睡去,梦里那个孩子又来了。
这次他伸出冰凉的小手,轻轻碰了碰她的脸,而后转身沿着铁轨走去。她拼命想追,双脚还是像生了根。情急之下她喊出“林晨光”,那孩子竟真回过头来,冲她甜甜一笑,又摆了摆手。
就在孩子转身离去的瞬间,梦醒了。她摸到枕上一片湿凉,分不清是冷汗还是泪。
医院走廊里,消毒味和林志风身上的羊油膻混在一起,熏得郑美玲太阳穴直跳。她窝在候诊椅上,余光瞥见林志风又一次摸向裤兜——那个装着红梅烟盒的口袋。
这段时间,郑美玲的孕反减轻了不少。早上起来不再恶心,饭量也恢复了些。史秀珍乐呵呵地宽慰她,“这是迈过了三个月的坎,胎稳了。”
可她记得当初怀雪球的时候,正是这会儿吐得最凶,喝水都反胃。可现在,这份平静像是来得太快,太轻巧,反倒让她心里发毛。
“我出去抽根烟。”林志风到底是起身了。
郑美玲盯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安全通道,随后听见打火机“咔嗒”响了。
“胎停了。”医生说。
郑美玲反应了会儿,扭头仔细看了看b超屏幕。
是静止了,像张黑白照片。
郑美玲下意识望向门口,走廊尽头只有安全通道的绿灯在闪烁,不见林志风的身影。
“长期接触烧烤油烟会影响精子质量……”医生的声音忽远忽近,“当然也可能是孕妇营养不良……”
郑美玲盯着那个静止的小黑点,咬紧了牙关。
梦里晨光冰凉的小手。那不是安慰,是告别。
“手术还是先吃药看看?”
郑美玲回过神来,局促发问:“吃药……更便宜吧?”
“是便宜些。”医生叹了口气,“但要是不干净,还得来刮宫。”'b超探头在她肚皮上轻轻敲了两下,“遭两茬罪。”
药房窗口的玻璃映出她发青的脸。
当护士递出米非司酮药盒时,林志风才带着一身烟味晃回来,“刚碰见小学同桌,约好晚上去咱那去喝酒。”他瞥了眼郑美玲接过的几个药盒,“这啥药?”
郑美玲刚要答,林志风就摸着下巴新冒的胡茬,继续开口,“你说怪不怪?二十年没见的老同学,偏在妇幼医院门口碰见。”
身旁的人们来来往往,郑美玲把药盒依次塞进包底,沉默伫立。
“人家开大奔来的,”林志风还在絮叨,“我说这顿必须我请……”
郑美玲望着丈夫上下翻动的嘴唇,在那一刻,她恨上了他。
她想起林志风把攒下的两千块塞给老舅时挺直的腰杆,想起他总说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”,他要面子,可她却舍了脸皮去爬火车偷煤,在警铃大作的夜里吓得脏了一缸酸菜。
她冷不丁笑了。
笑她嫁了个把面子焊在骨头里的蠢货,笑她为省半袋煤钱在火车皮上抖成筛子,笑她此刻攥着廉价堕胎药,而眼前这个男人正盘算着把钱拿来给陌生人免单。
她又想起了林长贵那副临死前枯树一般的身体。
这男人用孝心压垮了全家脊梁,用虚名榨干了最后滴血,连未成型的骨肉都成了他“有情有义”的祭品。
第二天一清早,林志风昨夜招待大奔故友时喝的酒还没醒,郑美玲在家服下了那粒米非司酮。
可那盒药在茶几上放了那么久,林志风擦桌子时甚至掸落过上面的烟灰,却始终没发现“用于终止妊娠”这几个字。
于是她把它塞进了衣柜里那件枣红色大衣的口袋。
等到林志风回来,她说:“柜子里樟脑放多了,那件枣红大衣帮我拿出来放放味儿,我过年要穿。”
第25章 25 老林离家出走了
那之后的两天,林志风再没踏进家门。他每天下午照常开店,夜深了就蜷在七十岁老娘的炕梢凑合过夜。
林雪球打电话问起,他只说史秀珍这几日血压不稳,得留下照应。
电话这头,郑美玲捧着本菜谱装模作样地翻看,耳朵却悄悄支过来,连书页都忘了翻。
二十年前的年根儿,也是这光景。
药盒的“秘密”终于被发现,俩人爆发了最激烈的争吵后,林志风白日里仍回来做饭熬药,入夜却再见不到人影,当时郑美玲的说辞也是奶奶身体不好,爸爸要去照顾。
那年除夕的爆竹声格外喧闹,满桌菜肴冒着虚假的热气,大人们强撑的笑脸后藏着心照不宣的离别。只有十岁的她,还傻乎乎地往新棉袄兜里塞满糖果,以为这样的团圆会永远继续下去。
“多余和他讲这些。”郑美玲将书一合,躺在沙发上,扯过沙发上叠好的棉被时,她嘟囔了句,“棉被咋这么薄。”
林雪球心里是不担心的。无论是今时,还是二十年前,林志风的“离家出走”都并非源于恨,他只是无法面对郑美玲。
在雪球的记忆里,那段日子母亲总是躺在炕头或蹲在卫生间,炕沿那提卫生纸耗得飞快,装着血污纸团的垃圾袋似乎永远也丢不完。
小年那天,史秀珍风风火火闯进来,一手拽着雪球,一手架着裹成粽子的郑美玲就往卫生所赶。
诊室里飘来“没流干净”“得刮宫”的只言片语,夹杂着奶奶数落母亲 “糊涂”的声音。
当郑美玲被搀出来时,雪球正蹲在雪地里堆雪人,抬头间看到母亲的脸竟比雪人还要惨白。
那晚林志风终于回了家。
雪球趴在里屋写作业,听见外间传来奶奶絮絮的复述:“没流干净”“刮宫”,当那句“为省几个钱没去医院”砸下来时,父亲爆发的抽泣声像把钝刀,生生剁开了夜的寂静。
后来雪球才懂,父亲的心知肚明。婚姻的破碎从来不在那个未出世的孩子,而在自己的无能。
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母亲离开后,父亲总在深夜抱着酒瓶对着电话痛哭忏悔。有次雪球听见他喊着“美玲啊”,她急忙抢过听筒,却发现那头只有空洞的忙音。
多年后回望,雪球更能看清那些被烟火气掩盖的残酷。
在煤灰与油烟熏染的每一个清晨与深夜,他们早就在油腥里熬成了两具空壳,却还要互相撕扯着仅剩的血肉,去填生活的窟窿。
她看到的其乐融融,不过是精疲力竭后的相互依偎,是绝望中强撑的笑脸。
郑美玲的离开,从不是突然的决定,她是经年累月磨损后,终于绷断了弦。
林志风不着家的时光里,瑜伽垫成了母女俩交心的场所。
电视里播放着郑美玲特意下载的孕妇普拉提视频,林雪球第一次向母亲完整讲了她和石磊的故事。
郑美玲轻松劈出一字马,动作流畅得不像五十岁的人,“闹了半天你压根不喜欢人家啊。”她调整着呼吸节奏,“本来觉得石磊那小子不是好东西,现在看来,你也强不到哪去。”
另一边,林雪球僵得像块木板,活脱脱就是史秀珍的翻版,“妈,你这话说得也太难听了。”
“你自己说的,图他可靠,图他对你好。”郑美玲掰着手指细数,“平时就手机聊聊天,月末见个面,吃吃饭看看电影。”
“我工作那么忙,月末能抽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!”
“月末见面是因为不忙吗?”郑美玲一掌拍在林雪球后腰上,帮她调整姿势,“那是因为排卵期到了!”
林雪球猛地回头,正对上母亲意味深长的目光。她眯着眼睛,嘴角挂着洞悉一切的笑,“吃饭看电影之后的事,不用我细说了吧?不然这小崽子哪来的?”
电视里的教练还在温柔地指导呼吸,母女俩之间的空气却安静了。
林雪球还在琢磨母亲怎么把自己生理周期记这么清楚,郑美玲已经利落地换了姿势,仰头望着天花板继续分析:“不说别的,这都多少天了,就看你哭过一回,还是因为我和你爸在饭桌上掐架。”她鼻子喷出声轻哼,“真要动过感情,就算死心了也不可能一滴眼泪都不掉。”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