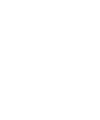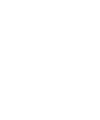击中你的心(1v2) - 第十六章替代
第十六章 替代
沉家训练馆的灯光是惨白色的。
不是学校体育馆那种带点暖黄的照明,也不是叶家私人场馆里可调节的柔和光线,而是彻彻底底、毫无遮掩的冷白。每一盏灯都亮得刺眼,将剑道、墙壁、乃至空气中漂浮的灰尘都照得无所遁形。林见夏站在剑道一端,感觉自己像实验台上被解剖的标本。
“手腕,再高两厘米。”
沉恪的声音从场边传来,不高,却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进空气里。他坐在高脚椅上,手里拿着平板,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林见夏动作的角度数据。
林见夏咬紧牙关,调整持剑姿势。她的手臂已经开始发酸——保持同一个标准姿势十五分钟了,沉恪的要求是肌肉必须形成绝对精准的记忆。
“左肩,沉了0.5度。”
她立刻修正。
汗水顺着额角滑下,滴进眼睛里,刺得生疼。但她不敢擦,因为沉恪说过,训练时要习惯汗水干扰视线的情况——“赛场上没人会为你喊暂停”。
“休息三十秒。”
终于。
林见夏放下剑,大口喘气。她走到场边拿起水瓶,手却在微微发抖。不是累,是紧绷——这种每分每秒都被监视、被纠正、被数据化的训练方式,让她有种窒息感。
“才第一天,就受不了了?”
冷淡的声音从旁边传来。
林见夏转过头,看到沉司铭靠在墙边,手里也拿着一瓶水。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训练内容,白色训练服被汗水浸透,紧贴着他精瘦却线条分明的身体。他的呼吸平稳,显然对这种强度习以为常。
“没有。”林见夏简短地回答,拧开瓶盖喝水。
“你的心率比正常值高了15%。”沉司铭看了眼她手腕上戴着的监测手环——沉恪要求两人训练时必须佩戴,“紧张?还是不适应?”
林见夏没说话。
她确实不适应。不适应没有叶景淮的训练。
以前在叶家场馆,即使训练再累,中途休息时总有人递来恰到好处温度的水,总有人用毛巾帮她擦汗,总有人在她某个动作做得好时笑着揉她的头发说“漂亮”。那些细小的、温暖的互动,像训练间隙的甜点,让她有力量继续苦熬。
但在这里,什么都没有。
只有冰冷的灯光,精准的数据,和沉恪永远没有起伏的指令声。
“第二组,基本步伐,开始。”
沉恪的声音再次响起。
林见夏放下水瓶,重新走回剑道。她需要完成二十组弓步冲刺,每一组都必须达到标准的速度、力度和角度——传感器会实时反馈数据,不合格就要重来。
第一组,通过。
第二组,通过。
第三组……
“速度慢了0.2秒,重来。”
林见夏深吸一口气,退回起点。
第四组,她拼尽全力,冲刺的瞬间感觉小腿肌肉都在尖叫。
“通过。”
第五组,第六组……到第十二组时,她的呼吸开始紊乱,肺部像着了火。
“呼吸节奏乱了,调整。”
她强迫自己控制呼吸,但越紧张越乱。
第十三组,失败。
第十四组,失败。
“停。”沉恪从高脚椅上下来,走到剑道边,“林见夏,你的注意力呢?”
林见夏摘下面罩,汗水像小溪一样从脸颊淌下。她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却发不出声音。
“我说过,训练时必须百分之百专注。”沉恪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,但声音里的冷意更重了,“如果你脑子里还在想别的,现在就可以离开。”
“我没有……”林见夏的声音有些哑。
“你有。”沉恪打断她,目光锐利如剑,“从第三组开始,你的视线有七次不自觉地飘向门口。你在等什么?等叶景淮来接你?”
被说中了。
林见夏的脸瞬间涨红,不是羞耻,是愤怒——一种被赤裸裸剖开、毫无隐私可言的愤怒。
“沉教练,我——”
“我不管你和叶景淮是什么关系。”沉恪的声音斩钉截铁,“但在我的训练馆里,只有击剑。如果他的存在会影响你的专注,那他就不该出现。这是我的规矩。”
林见夏握紧了拳头,指甲深深陷进掌心。
“继续。”沉恪转身走回座位,“从第十三组重来。”
接下来的训练,林见夏拼尽了全力。她强迫自己不去想叶景淮,不去想那些温暖的过往,把所有情绪都压进心底最深处。但越是这样,她的动作越僵硬,失误越多。
第二十组弓步冲刺结束时,她的腿已经软得几乎站不住。
“勉强及格。”沉恪在平板上记录着数据,“今天的体能训练到此为止。休息十分钟,然后和司铭打三场实战。”
林见夏瘫坐在地上,连走去场边的力气都没有。
沉司铭走过来,在她面前蹲下,递来一瓶新的电解质水。
“喝这个,恢复得快些。”
林见夏接过水,手还在抖。她拧了好几下才拧开瓶盖,仰头灌了大半瓶。
“你不该分心。”沉司铭的声音很平静,“我爸最讨厌训练时不专注的人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林见夏的声音闷闷的,“但我控制不住。”
“为什么?”沉司铭问,目光落在她汗湿的脸上,“叶景淮就那么重要?重要到没有他在旁边,你就不会训练了?”
这话问得直白,甚至有些刻薄。
林见夏抬起头,瞪着他:“你根本不懂。”
“我是不懂。”沉司铭站起身,居高临下地看着她,“我不懂为什么有人会把击剑这么纯粹的事,和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搅在一起。”
“乱七八糟?”林见夏也站起来,因为体力不支晃了一下,但还是挺直背脊,“叶景淮对我来说不是‘乱七八糟的东西’。他是我的男朋友,是我最——”
沉司铭打断她,嘴角勾起一个近乎嘲讽的弧度,“那他怎么不在?他不是应该陪着你,支持你吗?”
林见夏愣住了。
“因为他尊重我爸的规矩。”沉司铭继续说,声音压低了些,“因为他知道,真正的支持不是黏在旁边说好听话,而是给你空间,让你自己成长。”
这话像一记闷棍,敲在林见夏心上。
她想起叶景淮送她来训练馆时说的话:“见夏,这是你的路,你得自己走。我会在每一个里程碑等你,但过程,你得自己熬过去。”
当时她觉得这话很温柔,很体贴。
现在才明白,这话里有多少无奈和不舍。
“休息时间结束。”沉恪的声音传来,“实战准备。”
林见夏用力抹了把脸,重新戴上面罩。
三场实战,她输得很惨。
不是技术问题,是心态。她的注意力始终无法完全集中,每一次出剑都带着急躁和憋闷,被沉司铭轻易看穿、化解、反击。
第一场,7:15。
第二场,5:15。
第三场,4:15。
一场比一场差。
“停。”沉恪叫了暂停,走到剑道上。他没有看林见夏,而是看向沉司铭:“你在干什么?”
沉司铭摘下面罩:“正常对抗。”
“正常?”沉恪的声音冷了下来,“她的动作全是破绽,情绪完全失控,你打的这叫正常对抗?这叫虐菜。”
沉司铭抿紧嘴唇,没说话。
“重来。”沉恪转向林见夏,“这一次,我要你忘记所有杂念。把剑道当成战场,把对面的人当成你必须杀死的敌人。如果你做不到,今晚就不用回去了。”
林见夏的心脏狠狠一缩。
她重新摆好架势,透过面罩网格看向对面的沉司铭。他也重新戴上了面罩,但隔着网格,她仿佛能看到他眼中那抹复杂的情绪——不是嘲讽,不是轻蔑,而是一种……审视?
“开始。”
林见夏动了。
她用尽全力冲刺,剑尖直指沉司铭胸前。这一剑很快,很猛,带着压抑了一整晚的愤怒和委屈。
沉司铭侧身格挡,金属撞击声清脆刺耳。
但林见夏没有停。她像疯了一样连续进攻,一剑接一剑,完全不顾防守,完全不顾节奏,只是单纯地、发泄般地攻击。
“嗒!”
“嗒!”
“嗒!”
奇迹般地,她竟然连续得了三分。
但第四剑,沉司铭的反击来了。他的剑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刺出,绕过她凌乱的防御,精准地点在她的肋侧。
林见夏的动作僵住了。
不是因为被刺中,而是因为这一剑的角度、力度、时机……和叶景淮教她的一模一样。
那个瞬间,她仿佛看到了叶景淮站在对面,用他惯用的方式破解她的进攻。
分神了。
沉司铭的下一剑紧随而至,刺中她的手臂。
然后是第三剑,第四剑……
比分被迅速追平,反超。
当沉司铭的剑第十五次刺中她的有效区时,林见夏摘下面罩,狠狠摔在地上。
“我不打了。”
她的声音带着哭腔,眼泪混着汗水一起流下。不是因为输,是因为无力——那种拼尽全力却依然溃不成军的无力感。
沉恪走过来,捡起地上的面罩,递还给她。
“捡起来。”他的声音没有任何波澜,“比赛还没结束。”
“我说了我不打了!”林见夏提高音量,眼睛通红,“这种训练有什么意义?我像个机器人一样被纠正,像个傻子一样被虐,我受够了!”
沉恪看着她,沉默了足足十秒。
然后,他开口:“如果你现在退出,我不会拦你。但你要想清楚,走出这个门,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接受国内最高水平的指导。你的天赋,你的潜力,都会止步于此。”
林见夏的嘴唇在颤抖。
“选择权在你。”沉恪转身,走回场边,“司铭,收拾器材。今天的训练提前结束。”
沉司铭看了林见夏一眼,开始默默收拾散落的剑和面罩。
林见夏站在原地,看着沉恪走向办公室的背影,看着沉司铭弯腰捡剑的身影,看着这个冰冷、严酷、毫无温度的训练馆。
她突然想起第一次拿起剑时的情景——在叶家场馆,叶景淮手把手教她握剑的姿势,阳光从窗户洒进来,照在他温柔的侧脸上。
“击剑很好玩的。”他当时笑着说,“像跳舞,又像打架。”
可现在,一点都不好玩。
这不像跳舞,像受刑。不像打架,像被单方面碾压。
她蹲下身,抱住膝盖,把脸埋进去。眼泪不受控制地涌出,打湿了训练服的裤腿。
不知过了多久,一双运动鞋停在她面前。
林见夏抬起头,透过模糊的泪眼看到沉司铭站在那儿,手里拿着她的剑包和水瓶。
“给。”他把东西递过来。
林见夏没接。
沉司铭在她身边坐下,没有靠得太近,但也没有离得太远。两人就这样并排坐在剑道边,头顶是惨白的灯光。
“我第一次被我爸骂哭,是七岁。”沉司铭突然开口,声音很平静,“那时候我刚学击剑半年,参加了一个少儿比赛,八强赛输了。回家后,我爸让我对着墙练习基本步伐,练了四个小时。我累得站不稳,摔了一跤,膝盖磕破了。我坐在地上哭,以为他会来扶我。”
他顿了顿,继续说:“但他没有。他就站在那儿,看着我哭,然后说:‘哭完了吗?哭完了就继续练。赛场上没人会因为你哭就让你赢。’”
林见夏抬起泪眼看他。
沉司铭的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,下颌线紧绷,眼神深得像夜里的海。
“那时候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冷酷的人。”他说,“但现在我明白了,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,竞技体育有多残酷。眼泪没用,撒娇没用,就连痛苦本身——如果它不能让你变强,那就也没用。”
林见夏吸了吸鼻子,声音还带着鼻音:“所以你就习惯了?”
“习惯了。”沉司铭点头,“习惯了把所有的情绪都压下去,只留下对胜利的渴望。习惯了疼痛,习惯了孤独,习惯了……一个人。”
他说最后三个字时,声音几不可察地低了下去。
林见夏忽然想起,她好像从来没见沉司铭身边有特别亲近的朋友。在学校里他总是独来独往,在训练馆里永远独自加练,就连比赛时,别的选手都有家人朋友加油助威,而他只有沉恪冷静的指导。
“你……不觉得寂寞吗?”她小声问。
沉司铭沉默了。
良久,他才开口,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:“寂寞是奢侈品。我没资格要。”
林见夏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。
她看着他挺直的背脊,看着他紧抿的嘴唇,突然意识到,这个总是冷淡高傲的少年,或许并不是真的那么不可接近。
他只是……习惯了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。
“今天的训练,对不起。”沉司铭突然说,转过头看她,“我不该说那些话。叶景淮对你很重要,我知道。”
林见夏愣住了。
“但我爸说的也有道理。”沉司铭继续说,目光落在远处的剑道上,“如果你想走到最高处,就必须学会独自面对这一切。依赖别人,会成为你最大的弱点。”
“可我不想一个人。”林见夏的声音又带上了哭腔,“我不想失去叶景淮,不想失去那些温暖的、美好的东西。击剑很重要,但那些也很重要啊……”
“没人让你失去。”沉司铭说,声音里带着一种罕见的耐心,“只是……暂时放下。等你能在剑道上站稳了,等你能独当一面了,那些东西还会在的。如果它们真的属于你的话。”
这话说得理智,甚至有些冷酷,但林见夏听出了其中隐藏的安慰。
她擦了擦眼泪,深吸一口气:“你说得对。我不能总是依赖叶景淮。”
沉司铭点点头,站起身,向她伸出手。
林见夏看着那只手——手指修长,骨节分明,手心有长期握剑留下的薄茧。她犹豫了一下,还是握住了。
他的手很暖,有力,稳稳地将她拉起来。
“下周的训练,我会认真。”林见夏说,声音还有些哑,但眼神已经重新变得坚定,“不会再分心了。”
“嗯。”沉司铭松开手,提起她的剑包,“我送你到门口。”
两人一前一后走出训练馆。秋夜的风迎面吹来,带着刺骨的凉意。林见夏裹紧了外套,突然想起什么,转头问沉司铭:“你爸为什么不准叶景淮来?真的只是怕我分心吗?”
沉司铭的脚步顿了一下。
路灯的光从他头顶洒下,在他脸上投下深深浅浅的阴影。他的表情在明暗交界处看不真切。
“有一部分是。”他说,声音在夜风中有些模糊,“但更多的……我觉得他是想让你切断对叶景淮的依赖,彻底进入他的训练体系。”
林见夏皱起眉:“什么意思?”
“意思是,在我爸的世界里,只有两种人:他掌控的,和他无法掌控的。”沉司铭看向她,眼神复杂,“叶景淮选择了退出,选择了他无法掌控的道路。而你还在这个体系里,所以他要把你完全拉过来,让你只相信他,只听他的。”
这话说得直白,甚至有些残忍。
林见夏的后背升起一股寒意:“那他……把你当成什么?”
沉司铭笑了,那笑容里没有一点温度:“作品。最得意的作品。”
两人走到公交站,最后一班车还没来。站台上空荡荡的,只有他们两个人。
沉默在夜色中蔓延。
良久,林见夏轻声说:“今天谢谢你。陪我说话。”
“不用谢。”沉司铭靠在广告牌上,抬头看着夜空,“反正我也没事。”
“你……”林见夏犹豫了一下,还是问出口,“你平时训练结束都做什么?直接回家吗?”
“嗯。或者加练。”沉司铭说,“偶尔会去便利店买点吃的。”
“一个人?”
“一个人。”
林见夏的心又软了一下。她想起叶景淮,想起他们训练结束后总会一起去吃宵夜,一起吐槽教练,一起规划周末的安排。那些平凡琐碎的时光,原来这么珍贵。
“其实……”沉司铭突然开口,声音很轻,“如果你真的不习惯一个人,我可以陪你……”
他顿了顿,似乎在斟酌用词。
林见夏转头看他。
沉司铭的眼睛在路灯下闪着微光,那里面有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情绪——不是冷淡,不是审视,而是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。
“我可以陪你训练。”他终于说出口,语气故作轻松,“反正我爸让我当陪练,那我就当得彻底一点。训练间隙,我们可以……说说话。聊击剑,或者别的什么,就你和叶景淮平时聊的那些。”
林见夏愣住了。
这个提议太意外了。沉司铭,那个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沉司铭,主动说要陪她?
“你不用这样。”她小声说,“你已经有自己的训练计划了,不用特意——”
“不是特意。”沉司铭打断她,声音重新恢复了平时的冷淡,“只是我爸说得对,教你的时候,我自己也能学到东西。互惠互利而已。”
他说得轻描淡写,但林见夏看到了他耳根微微泛红。
公交车来了,车灯刺破夜色,缓缓停靠在站台前。
“车来了。”沉司铭把剑包递给她,“下周见。”
林见夏接过包,走上车。在车门关闭前,她回过头,看到沉司铭还站在站台上,灯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,孤独地投射在地面上。
公交车启动,他的身影迅速后退,消失在夜色中。
林见夏坐在靠窗的位置,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城市灯火,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。
这一天的训练很痛苦,很煎熬,但最后那段对话,却像黑暗中的一点微光,让她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
沉司铭并不像表面那么冷漠。
而他说的那些话,虽然冷酷,却都是事实。
如果她想走得更远,就必须学会独自面对。
但“独自”不代表“孤独”。
也许……也许沉司铭可以成为那个训练馆里的同伴。不是替代叶景淮,而是填补叶景淮离开后留下的那片空白。
公交车在夜色中平稳行驶,载着少女,驶向未知的明天。
而站台上,沉司铭在车开走后,又在冷风中站了很久。
直到手机震动,沉恪发来消息:【还不回家?】
他这才转身,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脚步很慢,很沉。
有些东西,正在悄然改变。
有些界限,正在模糊。
添加书签
搜索的提交是按输入法界面上的确定/提交/前进键的